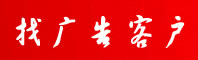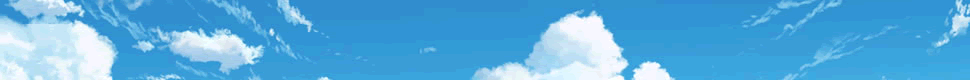当前位置:中国广告人网站>创意策划>创意文案>详细内容
广告语言的文化批判3
作者:佚名 时间:01-4-2 字体:[大] [中] [小]
-
广告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仪式,它成了人们每天都必须“参与”的“布道”,因为广告这种符号活动与一种潜在的“宗教”——拜物教——密切相关。但是,有一点看来值得深究,即作为一种纯粹的商业性诉求活动,广告的心理学功能在于最终说服和打动受众对某种商品的认可,进而驱使他们产生购买和消费行为。
这种赤裸裸的商业心理学功能,却往往是在其语言极具迷惑性的诗意运用中实现的。换言之,广告语言的诗意模仿具有反诗意的本性。国内的广告目前已经告别了最初直白式的诉求,进入一个追求雅致和风格的语言表达阶段。于是,直接
语言是我们赖以生存在的家园。通过对事物的命名,语言召唤了存在,并使之呈现于无蔽的状态之中。语言的这种功能最明显地反映在诗意的语言中。所以,海德格尔说,诗人是我们家园的守护人。那么,广告语言如何呢?显然,它与其说是呈现一个世界,不如说是蒙蔽了世界;与其说是凝定了存在,不如说是放逐了存在;与其说是为存在命名,不如说是为欲望命名。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符号,具有基本的命名功能。伽达默尔指出:“这里有一种对当下的距离,一种对于将临之事的瞻望。人并非仅仅被给予或提供眼前之物来对我们造成作用。正如我们在语言的本质中所发现的,语言是一种距离。
”[(3)]我以为,语言的距离是诗意语言本质。在诗的语言中,诗人对事物的命名,使之从遮蔽状态中走到无蔽的呈现之中。但是,在诗的语言中,语言在呈现存在时,并不在于使人对所呈现的事物有一种直接的占有欲,相反,它使人们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审美距离)静观事物,发现其存在样态和变化,观照其作为物的物性自然显现。在这个特定的比较意义上说,诗的语言是一种有距离的
语言,它在对事物的命名中,在对存在的揭示中,形成了超越性。它通过命名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在体认事物存在的同时,进入了更加广大的想象空间自由翱翔。但广告语言在多方面则完全不同,比较而言,它是一种要消灭距离的语言。
在广告的语言表述中,核心问题是如何使语言这种抽象的符号紧密地和某种特定的商品联系在一起,甚至作为它的符号表征。这样一来,广告语言的基本功能就不是距离,而是同一。它所导致的看似丰富的各种意义,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地回归到商品的品牌及其有用性上。它所导致的“诗意的唤起”,最终却以消灭“诗意”为目的,即对商品的欲望是压倒一切的考虑。这表明,在广告语言中,诗意的真正用途正在于反诗意的本性。因此,它就显然只是一种限制性的语言,而不是超越性的语言,因为,在它的直接诉求中,受众的想象力被遏制了,无一例外地被引向某商品及其占有的欲望上。正是如此,它对事物(商品)的命名,实际上不是对事物的事物性的揭示,不是对物的存在的敞亮,相反,其命名是对物所以为物的存在的遮蔽。
另一方面,诗的语言是一种事物的语言,诗人在其 中作为守护者,是把事物自身显现出来,让事物自己说话。诚如伽达默尔指出的:“事物是有自己存在的东西,像海德格尔所说:是‘不能强迫它什么都做’的东西。事物自身的存在由于人所想操纵事物的专横意志而被忽视了,它就像一种我们不能不听的语言。”
[(4)]即是说,诗人是最善于倾听事物语言的人,他们把听到的东西告诉我们,他们是让事物自己说话。唯其如此,我们在诗里听到大自然的呼唤、倾诉和哀怨,我们听到了万事万物用它们自己的声音在说话,我们聆听着一切有生命的甚至无生命的造物的脉搏。这就构成了诗人和自然以及我们和诗人之间的真正的对话,“变成了语言的诗的结构保证了灵魂和世界作为有限东西相互诉说的过程”[(5)]。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一下广告语言,就会发现,诗意语言的这种品格不复存在了。在广告里,事物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不是事物自己在说话,而是商品的推销者在说话,这种话语旨在让人去消费物的有用性,于是,即使具有诗意的表达方式,说穿了不过是这些人的“叫卖声”而已。诗意的语言又一次被用来反对诗意的本质,潜藏在诗意语言之下的原本是一些强烈的拜物意识形态。
广告语言的诗意运用的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它典型的“得意忘言”的特征。诗的语言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不但昭示了世界,同时还显现着自身。即是说,在诗意的语言中,人们不但把握了它所表现的世界,同时还体味着这种独特的语言自身的魅力,叹服于诗人驾驭语言的本领和鬼斧神功的创造。然而,在广告中,尽管诗意的手法司空见惯,可诗的语言的这种特征却荡然无存。广告语言的诗意模仿,主要目的是在传达一种商品信息的同时激发出受众的购买欲望。
情感的诉求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物欲,而语言不再像诗的经验中那样处于前景,而是退到背景,处于前景的唯一角色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商品。更有趣的是,在广告中,语言不仅自身处于后退的境地,而且,在电视、印刷等广告形式中,语言已经从主导的表达方式,蜕变为一种辅助性的提示语。即是说,在形象或影像的强大视觉冲击力面前,广告语言通常扮演着某种程度的“配角”,这和诗意语言的本质是绝对不相容的。我们在影像的诱惑面前,恰恰忘却了语言。